1999年5月19日,二十年前的这一天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唯一能激起人们回忆的是这一天被后来称为股市5.19纪念日,从这一天开始,中国股市启动了迄今为止最为壮观的一轮牛市行情。然而,正是在这一天的18时34分,散文作家苇岸因肝癌医治无效辞世,享年39岁。在去世以前,他于病中写下了最后一则《廿四节气:谷雨》。
按照苇岸生前的意愿,亲友们将苇岸的骨灰伴着花瓣撒在故乡的麦田、树林与河水中。之于我们这个时代,苇岸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生活在“天明地静”的京郊昌平,生前只留下了一部作品《大地上的事情》,又在病榻上编就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太阳升起以后》,次年5月出版于中国工人出版社。

《大地上的事情》,苇岸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苇岸曾在《大地上的事情》里说,“想起一些遥远的、渐渐陌生的事物:农夫、渔夫、船夫、樵夫、猎户、牧人、采药人、养蜂人。它们属于已经逝去的世纪,这是一些词和职业,也蕴含着另外的意义:它们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桥梁。”终其一生,他将歌颂大地视为是自己的责任,也让他成为了中国当代书写自然文学的先行者。在梭罗的《瓦尔登湖》感召之下,他以独立的立场,保持着对自然的欣赏和审视。

苇岸,原名马建国,1960年1月生于当时的北京市昌平县北小营村,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2年在《丑小鸭》发表第一首诗歌《秋分》,1988年开始写作开放性系列散文作品《大地上的事情》,成为新生代散文的代表性作品。1998年,为写《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苇岸在家附近选择了一块农地,在每一节气的同一时间、地点,观察、拍照、记录,最后形成一段笔记。1999年在病中写出最后一则《廿四节气:谷雨》,5月19日因肝癌医治无效谢世,享年39岁。
林贤治将苇岸视为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圣徒”,而在同为散文家一平的眼中,他同样是一位圣徒,“他的诚恳、温暖、善良,以及他的谦卑、清苦和忧郁。他是罕有的人,清洁得透明,想到他就会想到北方的清晨和田野。放下宗教,由人性而言,他是那种以善、清苦、信念来完成生命的人。”一平认为,《大地上的事情》是一部远超时代的作品,即使今天的我们,依然难以看清,与梭罗笔下原始自然的“瓦尔登湖”不同,苇岸笔下的“大地”更加意味深长,“寓意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
王家新曾说苇岸是“一位以他的生活和写作向我们昭示生命之诗的诗人”,散文只是他在文体上的贡献。他那充满诗意和哲思的言语,影响了许多活跃在当今文坛的作家、诗人,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土地诗人。苇岸曾感叹“这是一个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美好的时代”,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人类的增光者”。也难怪宁肯将他视作是“当今市井习气、后现代语境中的一道风景、一座孤岛”,在这个喧嚣的工业文明社会里,苇岸将自己的目光投诸自然生态,漫游四方,守望大地,最终,在离开了土地之后,他又回归了土地。
在苇岸逝世二十周年的今天,一本汇集了林贤治、林莽、树才、一平、宁肯、王家新、刘烨园、周新京等一众苇岸师友的纪念文集《未曾消失的苇岸》,得以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从不同侧面回忆和记录苇岸思想、写作、生活的文字,可以让我们再一次认识这位颇有盛名的散文作家。他所提倡的“土地道德”,之于二十年后的我们,依然有着积极而深刻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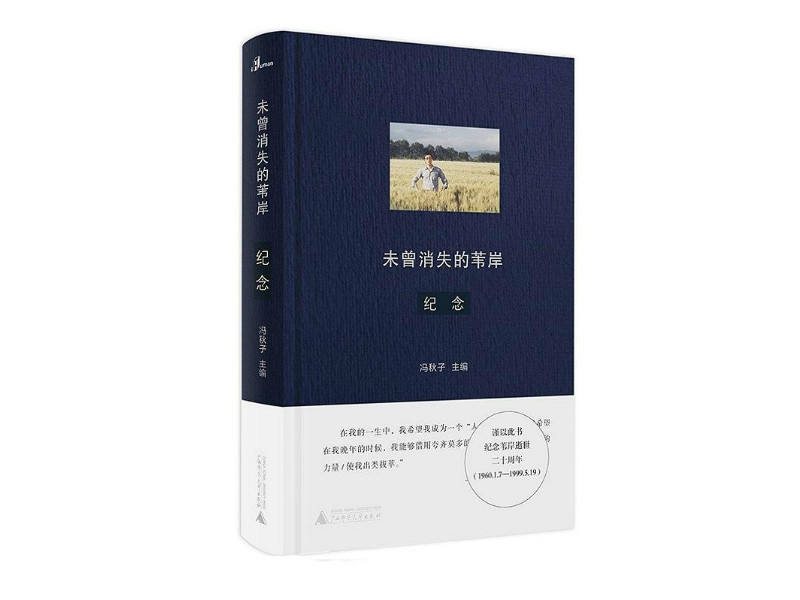
《未曾消失的苇岸》,苇岸等 著,冯秋子 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版。
以下内容摘自《未曾消失的苇岸》一书,内容较原文有删节。
《大地上的事情》再也不能续写
你在治病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写作,你精心准备了一年之久的《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已经写到了《谷雨》,每当你感到精神稍好时,你就要写下去,你想把它们完整地留给读者。你写得很艰难,不长的一段文字,你写了好几天,每当写完一小段,有了一些进展时,你都感到很欣慰。当《谷雨》终于写完时,你松了一口气,“廿四节气”四组你终于写完了一组。你还想把它们全部写完,没想到命运并不给你留下充足的时间。
一天,你躺在床上,把我叫到你的跟前。你说:“其他事已和妈说过,这件事就跟你谈谈。等我走的时候,身上就穿我那套西装,脚上就穿现在穿的那双皮鞋,衣服和鞋都没穿过几次,全都很新不用再换。告别那天肯定会有朋友来,不要花圈,不戴黑纱,也不要骨灰盒,我阳台上有两个菜坛,捡好一点的一个洗干净用就行了。骨灰就撒在我以前回老家骑车经常路过的东河边上的麦田里,河套边上的小树林里也撒上一些。这事只你和弟弟、妹妹同前去的朋友一起办就行了,不要惊动外人、引起别人的围观。大哥,这事就交给你办了。”
死神在悄悄地向你走近,你预感到在世时日不多,把妹妹找来,帮你整理所需要的资料。你躺在床上口述,妹妹在一旁记录,说几句就要休息一会儿。这样持续了三四个晚上,你的生平年表和最后几句话整理完,由妹妹用电脑敲了出来,而你此时的身体更差,双脚开始浮肿。
多年来你一直是素食,从不沾荤腥,面对你极度虚弱的身体,大家都劝你吃一些荤食,以增加身体的营养和抗病能力。你虽然接受了大家的劝告,但在吃荤食时脸上又透着那么明显的无奈,到最后你对这一改变很后悔,在你留下的《最后几句话》里,把这一改变视为你今生最大的懊悔,是信仰上的一种堕落。
五月十五日,你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肝部难受加剧并伴有疼痛,以前总是闭着的双眼也睁了开来,夜里基本上睡不着觉,说话也比以前多了许多。但我慢慢地发现,你说的话有时我已听不懂——你已经有了昏迷现象。
这天早上,母亲过来,劝说你住进昌平医院,说已安排好了,十八日可以住进去。这时你说的话又让我落下了眼泪:“去就去吧,我也该走了。”十七日下午,林莽大哥和宁肯来到你的住处,他们是来整理并带走你的书稿,以前说几句话就嫌累的你,与他们谈了近两个小时,我不知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你。夜里,你的昏迷现象加重了。
十八日,你住进了昌平医院,夜里我去医院陪你,你显得很痛苦,嘴里不停地说着、喊着,打完止疼针也不管事。天哪,我该怎么办?
你走了,我所祈求的奇迹没有出现,害怕看到的场面却来到眼前。五月十九日下午六点三十四分,我终生难忘。你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怔怔地站在你的床前,无情的病魔终于夺取了你的生命,你大睁着双眼似心有不甘。我知道你还有许多未了的心愿,只可惜今生再也无法把它们做完。《大地上的事情》再也不能续写,《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也成绝篇。
——马建山(苇岸哥哥) 二○○○年一月七日
遗憾“廿四节气”只完成了六个
二哥上中学时,喜欢上了文学,他的作品以描写大自然为主。二哥很喜欢大自然,每到放假,他都会出去旅行,去观察大自然,记下沿途的所闻所见。他对大自然的观察很仔细,记得有一次,二哥邀我一起出去踏青,他带我来到京密引水渠南边的一片麦田中,大约是五月,天气很好,麦苗已经很高了,当有微风吹过,麦田也随着起伏,麦田上空的电线上还停留着几只小鸟。这样的美景,使人心旷神怡,我从未想到这里还会有这么美好的景色。原来,二哥为了观察大自然,经常会到附近的田野中来,这个地方,他在不同的季节都来过,早已看到过这里在这个季节的景色,所以才会带我来。
二哥生病前,正在准备写作“廿四节气”,为二十四个节气中的每一个节气写一篇散文。为此,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做准备,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在每个节气日及前后几天,仔细观察当时的天气变化情况、庄稼的生长情况、大地上的昆虫及小动物的活动情况,并且在县城东部选取了一个固定地点(一片田地),在每个节气的当天,来这里进行拍照,记录下此地不同的节气所耕种的不同庄稼及它们的生长变化情况。记得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六日“小满”这个节气的前夕,二哥要去外地开会,无法在当天拍照,为此他很是犹豫,最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带我来到了他的拍摄地点,给我交代好他的拍摄位置、取景角度,并让我看了他之前在这里拍摄的其他节气的照片,让我在“小满”当天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在这里为他拍下照片。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放心,在第二天,即“小满”节气的前一天,他出发前,自己又来此预先拍下了一张照片。二哥去世后,我帮他整理日记时发现,有关于“廿四节气”的每一个节气,他已全部作了笔记,并冲洗出了照片。他最后抱病完成了一组六个节气的写作,而没完成其余十八个节气的写作,这成了他的遗憾。
二哥极少对家人介绍他在文学写作方面的情况。由于我较少接触文学领域,因此,在这一方面,我对二哥的了解,更多地来自他生病及去世后朋友们的介绍以及我对他的作品和日记、照片的整理。
二哥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很严格,写作很严谨。因此,他的写作很慢,作品很少。他曾在日记中写到,每写完一篇作品,就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在我处理他的作品有关事项的过程中,我也是按照他的原则来做的,每次,我都会问自己,我这样做是不是二哥希望的?对于二哥的日记要不要出版,我也一直在做思想斗争,这是不是二哥愿意做的事?二哥会同意吗?
——马建秀(苇岸妹妹) 二○○九年三月五日
未曾消失的苇岸
他的书,连同他一样是寂寞的。
说苇岸是一位作家,首先因为他是从人格出发,从心灵的道路上通往文学,而不同于一般的作家,是通过语言的独木桥走向文学的。是爱培养了他的美感,所以,语言在他那里才变得那么亲切、简单朴素而饶有诗意;所以,他不像先锋主义者那样变化多端,而让自己的文体形式保持了一种近于古典的稳定与和谐。对于他,写作是人格的实践活动,人格与艺术的一致性要求,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历史原点。这样的作家,注定要留在趋骛新潮的批评家的视野之外。
在苇岸的散文中,我们发现,关于具体的人事,他写得十分少,简直吝啬。而且这些文字,大体上是献给他的亲人和朋友的,完全出于情感的支配,仅是为海子写的就有数篇之多。但是,对于大自然,对于其中的许许多多的小生命,他乃不惜笔墨,描写种种细枝末节,充满关爱之情。这不是“齐物论”式的,不是物我两忘,也不是借物言志。他没有那种艺术的功利主义——把自然人格化,也许在他看来,这样的人类也太傲慢了。在他的作品中,人与自然是共时性的存在,是对等的、对话的,处在恒常的交流状态。在心灵的交流中,给予者同时也是获得者。爱作为观念,对苇岸来说是完全来自西方的,不是“三纲五常”的衍生物。这是博爱。平等、民主、公正,都是从这里辐射出去的。所谓人文精神,它的内核,就是对生命的爱。凡·高有一句话是苇岸喜欢的,说是“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他的散文写作,从发生的意义上说,无疑最接近艺术的本源。
苇岸自称“观察者”。他仔细耐心地观察大自然中季节的转换,对古老的时间有一种敏感。而他所掌握的时间,总是同播种、劳动、繁殖联系在一起的,直到生命终结,他仍然系念着与农事有关的二十四节气。没有形而上学的时间,他观察和赞美太阳、月亮、大地、小麦和自然中最可爱的生灵:胡蜂和各种蜂类、蝴蝶、麻雀、其他飞鸟、林木以及鸟巢……
尊重生命个体,彼此平等相待,是民主政治的人性基础。在生物界那里,他发现并描写了这种天性:善良,淳朴,谦卑,友爱,宽容,和平,同时把它们上升为一种“世界精神”,从而加以阐扬。
如何看待生命的原则?如何看待物质与精神?如何做一个诚实的人,而且彻底地诚实?在持久性的价值探索的旅途中,苇岸随同伟大的灵魂一起艰难跋涉。
“农村永恒”,这是他所不断祈祷和呼唤的。他反对美国式的农村城市化的做法,主张在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同时,保留农业文明的美好的遗产。这不是乌托邦,至少苇岸确信,一个作家,只有生活在俄罗斯乡村那样的地方才会写得好。他敢于幻想,但是深知希望的限度。在《进程》《马贡多与癞花村》等文章里,他反复揭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物质与精神的相悖现象。而他,是始终自奉俭省而忠于精神的。“在西方思想家那里,有一种说法:只有那些生活在一七八九年以前的人,才能体会出生活的美满和人的完整性。”他感慨地说道:“我觉得新时期以来的一二十年间,在精神的意义上,中国再现了西方几个世纪的进程。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美好的时代。”
世界为什么需要作家,如果作家不能够使自己变得美好的话?于是,我们见到,苇岸对自己的要求是那般严格,简直近于苛刻。临终前,他让他妹妹记下最后的话:“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在临终前,他请求说,在撒骨灰的时候,让友人能为他朗诵他所心爱的法国诗人雅姆的一首诗。诗的题目是《为他人得幸福而祈祷》。
这就是苇岸,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圣徒。
——苇岸著《太阳升起以后》序言,林贤治(诗人、学者、作家),一九九九年
以生活和写作昭示生命之诗
苇岸在本质上是一位诗人,一位以他的生活和写作向我们昭示生命之诗的诗人。人们说他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那是指他在文体上的贡献。实际上他的意义并不限于任何一种文类。他是属于那种在我看来在任何时代都不多见的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和诗人之一。与其说他找到了散文这一形式,不如说这一自由的形式正好适合了他——适合了他那罕见的质朴,适合了他对存在的追问,以及他对生命万物的关怀和爱。
请读一读他的《大地上的事情》(五十章)、《放蜂人》、《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等篇章,那里面有着金子一样的质地。那种质朴、硬朗、富于警策力和诗性光泽的语言,那种对事物本质的抵达,那里面所包含的灵魂和人格的力量,应该使这个时代的许多作家和诗人自愧。
我认识苇岸的时间并不长。几年前我们在什么场合见过,后来通过几次电话,相互寄赠过作品,仅此而已。但是,在他身上和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许多东西,都让我感到亲近。我知道这是一位可以信赖、可以深交的朋友。去年年中,我在昌平乡下建了一处北方乡村式的房子,并于今年年初搬了过去。这样,我与苇岸更近了。虽然我的村子距苇岸所住的县城尚有一二十公里,但一条清澈的沿着燕山山脉流过的京密运河却把两地联系在了一起(海子生前也很热爱这条河流,据苇岸的文章说,海子在赴山海关殉难的几天前曾彻夜在这条河的岸边徘徊)。
麦子是土地上最优美、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稼。麦田整整齐齐摆在辽阔的大地上,仿佛一块块耀眼的黄金。麦田是五月最宝贵的财富,大地蓄积的精华。风吹麦田,麦田摇荡,麦浪把幸福送到外面的村庄……
这是《大地上的事情》的第十一章。这就是苇岸为什么会立下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在他出生的村庄的麦地上。
同海子一样,苇岸也是直接抵达了生命和创造本原的诗人。他的《大地上的事情》,不仅抒写了他对万物的观察、感悟和热爱,而且也处处透出了内在的生命的光辉。他的语言目击了创造。他把麦地、树林、冬日的小灰雀,连同他自己质朴的生命,一起带入太阳的光流之中。因此,苇岸不仅安息在丰盛的麦地之中,也将永远活在那金子一样闪耀的语言之中。这一切,用苇岸自己所热爱的布莱克的一句诗来表述就是:“你寻找那美好的宝贵的地方/在那里旅人结束了他的征途。”(《啊,向日葵》)
——王家新(诗人、批评家、翻译家),原载《青年文学》二○○○年第五期
将写作“大地上的事情”作为终身目标
作品就是作家的一切。
苇岸为数不多的散文,篇篇值得用心去读,它们的汇集则成为一处独具特色的景观。他曾经撰文评价诗人海子的作品:“环顾四处,没有一个人能够走来,代替海子,把他的黄金、火焰和纯粹还给我们。”这话同样适合他自己。
他用一种和季节的递嬗更移一样的速度,艰难缓慢地写作。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斟酌,每一个句子都要再三修改,而每一篇文章的完成,都不啻一次艰难的历险。他是我见到的写得最苦的人。我想,这固然与思维的某种特别方式有关,但更是出诸他对自己的特殊要求。唯其如此,他才能够感知土地的脉跃、植物成长的节奏、雪花飘落和鸟儿飞翔的姿态。或者说大自然的内在韵律影响到他的写作,使他发愿让每个字都生动、准确、朴素,和土地的原态一样。
记得有一次,在电话中,我说到对他早期的作品《美丽的嘉荫》的喜爱,希望他继续写一些那样的情采并茂的文字,他却表示,他已经跨越了那个阶段,现在追求的是一种更加朴素的风格,它们集中体现在《大地上的事情》一文中。在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的信中——落款中他特意注明那天是夏至——就这个问题他进一步写道:“我敬重的一平,希望我的文字进一步具备容纳黑暗的深厚。我深思了这个问题,《美丽的嘉荫》那样的文字,也许适宜展示光明和美好,如果触及真实(这是我至今不愿走的一步),文字的方式必然有变。所以我说让其自然演变吧,如果写作真有鲜明的阶段性的话。”
就其努力来讲,应该说他达到了为自己确立的目标。《大地上的事情》,这不但被用作他的唯一的一部散文集的书名,不但是书中字数最长的一篇,更是贯穿他全部作品的一条主线,是开启他笔下世界的一把钥匙。数十则简短的文字,每一则都是对大地上初始的、最本色的、未曾受到玷污的事物的深情的一瞥,令看惯了陈词滥调的目光一亮,仿佛由冬日晦暗的幽禁中,直接走进初春蔚蓝的天空下。
经由那些简短的文字,他给人们看到事物的原初的美,它们或者已经或者即将毁灭于人类永无餍足的贪欲,或者被高科技时代的声光电遮蔽,无法传递出丰厚的蕴含。他的目标,便是用笔替它们开出一条道路。他要恢复大地的完整,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保存“世界最初的朴实和原质”。这种原初的面貌,是人类幸福的保证。这样,他很自然地将主张返归自然的梭罗、主张“根据资源许可来生活”的罗马俱乐部,和宣扬“土地伦理”的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引为自己的同道。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将写作“大地上的事情”作为终身的目标。
不知他是否明白,他瘦弱的躯体,担当起了怎样的一种艰难?可以说,西西弗斯的努力也不过如此。在工业化进程一日千里的今天,他所选择的是一条过于幽僻的道路,他的努力很可能徒劳,毕竟人们关心利润远过于诗意。我想,他是太清楚这样的后果了,但更清楚如果没有人为之呐喊告警,大地的荒芜就将更快地降临。他的声音在物欲的喧嚣声中是微弱的,但却绝对是必要的。
作为一名大地的守夜人,他自愿选择当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他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一步显露。
——彭程(作家、评论家),原载《散文天地》第六期纪念专刊,写成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太阳升起以后》 苇岸 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5月版。
(本文摘自《未曾消失的苇岸》一书,内容较原文有删节,章节为编者所加,已获得出版社授权。)
作者 马建山 马建秀 林贤治 王家新 彭程
摘编 何安安
编辑 沈河西 校对 薛京宁







